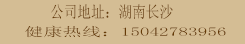![]() 当前位置: 淮北市 > 淮北市交通 > 金寨故事隐藏在红四名将周维炯身后的
当前位置: 淮北市 > 淮北市交通 > 金寨故事隐藏在红四名将周维炯身后的

![]() 当前位置: 淮北市 > 淮北市交通 > 金寨故事隐藏在红四名将周维炯身后的
当前位置: 淮北市 > 淮北市交通 > 金寨故事隐藏在红四名将周维炯身后的
隐藏在红四名将周维炯身后的“鬼妹”(一)
陈桂棣春桃
一、谁说女子不如男
被称作“鬼妹”的徐德英,小名英子。可以说,在当时的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和大别山的红军队伍中,她都称得上是一个最漂亮的山妹子。
她出生在商城县的洪湾,那地方最初还属河南省,解放后才被划归了安徽省。她的父亲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大山坳里的农民,婚后十多年,一直没有孩子,直到母亲三十岁那年,才有了她。见生的是个女娃,父亲先就叹了口气,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娃娃,还是疼爱得不行。尽管日子过得很艰难,有时糠菜也要当粮吃,他们却一心要把英子按有钱人家的女娃儿那样,把她培育成一个不须在土里刨食的人。因此,英子三岁时母亲逼她包小脚,七岁就将她送到叔叔教书的一所私塾里去识文断字。穷人的孩子没法讲穿戴,但她却是天生一副花容月色,聪慧水灵,让谁看到都会眼睛一亮:面如银盘,眼含秋水,轮廓清晰的鼻子既挺且直,特别是她那凝脂般白皙的肌肤,很是让人怜爱。
那时,邻村一个叫金兴江的富裕人家的孩子,也在那里读书。金兴江的父母见到英子的第一眼,就动了心,托了媒人,找到英子的父母,要给孩子订“娃娃亲”。早盼着英子长大成凰的父母,嘴上虽说“孩子还小”,心里却乐开了花。水往低处流,人朝高处走嘛!女儿能够嫁入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,一辈子雨不淋头,风不打脸,不愁吃,不愁穿,这是“攀了高枝”,于是约定:待英子私塾结业,金家就来迎亲。
“我不同意!”
这是徐德英第一次不容置疑地同母亲说话。
母亲伤心地哭了。说:“英子,你还小,什么都不懂,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啊!”
这年徐德英已经十二岁,在私塾里读了五年书,知道应该怎样去说服母亲。她说:“你们既然知道我还小,正在读书,就不该讲这些大人的事!”
母亲叹了口气说:“我知道你是一个心气高的孩子,可惜,你是个女孩子,要是个男孩子该多好,就可以出去干你想干的大事情。”
徐德英反驳说:“女孩子怎么啦?花木兰不照样替父从军么!”
母亲说:“好好好,娘说不过你,现在不跟你谈今后的事。”
这以后,母亲就不再谈她和金兴江的事,但徐德英却知道既然母亲把她和金兴江“娃娃亲”这事挑明了,显然是迟早回避不了的,一想到“长大”要同那个又高又瘦、毫无可爱之处的男孩子“厮守一辈子”,她就从心理到感情上都对金兴江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。
这天,徐德英一边帮母亲干活,一边心平气和地说:“笔架山学校又要招生了,我想去试试,叔叔那里的私塾不想再去了。”
母亲不识字,但不识字的母亲也知道,那所洋学堂虽建在深山老林的一座古刹里,老师却来自全国各地,名声很大,从那儿出去的学生是可以直考山外所有大学的。笔架山学校地属商城县,商城县的历届县长上任都要到那儿朝拜,鄂豫皖三省边区各县的人家无不把自己的孩子能在那读书引为骄傲。
“怎么,”母亲停下手里活,有些惊诧地问:“你想到那里上学?”
“想。”
母亲头也不再抬地说:“我不同意!”
“为啥?”其实徐德英并不意外。
母亲生气地说道:“我晓得你心里是咋想的。翅膀硬了不是,就一点听不进大人的劝告了?”
母亲知道英子硬要离开叔叔的私塾学校,去很远的笔架山读书,就是不愿再和金兴江接触,逃避这桩由双方父母做主的“娃娃亲”。
但是徐德英决心已下,对母亲说:“你若真不答应,女儿只有一条路。”
母亲见英子面色发暗,口气不一般,忙问:“啥路?”
徐德英说得斩钉截铁:“不跳塘,就投井!”
母亲被吓住了。她怕英子真的会这么做,不得不松了口:“你想去,就由你去试试。”
母亲所以这么快就松口,是因为她压根不相信女儿能考上那样的学校。早听说,那学校招的都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,她一个没有背景的女娃娃,也想去试,还不是白跑一趟。等到她白跑一趟回来,就会死了这条心。
不过,金兴江的父母却看得很清楚。他们的金兴江是考不上那所学校的,而徐德英不仅人长得出众,书也读得比儿子好,考上的可能性是极大的。他们就担心这只金凤凰要远走高飞了,远走高飞的英子就与自己的儿子毫无关系了。于是,二人慌忙跑到金家寨的街上,扯了几件衣料,又买了些生活必需品,送到徐家。
徐德英父母见了,很是感动。他们没有想到,这桩本不是“门当户对”的姻缘,金家会看得这么重,就很是为生了这个惹人喜爱的女儿感到欣慰,大包大揽地说:“放心吧,亲家,英子不管走到哪都是你们金家的媳妇。她一定要去笔架山报考,去也是白去,回来后我们就把她送到你们家里去!”
金兴江父母得了这样的许诺,自然也就不再说别的,放心地回去了。
徐德英发现了金家送来的东西,大为恼火,对父母不依不饶了。她把衣料和日用品狠狠地摔到地上,说:“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决定我的终身大事?明知我不喜欢他,非要把我嫁给他!”
母亲平日对宝贝女儿百依百顺,就认为这是惯坏了女儿,见她如此拒绝这门亲事,便沉下了脸,开导道:“英子,别看你读了不少书,人情世故上你还一点不懂,不说金家日子殷实,那孩子也有模有样,不呆不傻,又本分,他哪一点配不上你?你能嫁到这样的人家,已经是你的福分!”
徐德英见母亲这样说,又气又急,哭了起来:“反正我看不上他。你们再这样逼我,我就不回这个家了!”
母亲怔怔地望着徐德英,也伤心地哭起来。父亲却被徐德英的话激怒了,他指着徐德英,大声骂道:“混帐的东西!一点不听大人劝,除非你不认你的爹娘老子了!”
徐德英一赌气,提前去了笔架山学校。她走得很匆忙,许多东西都没带,却带走了那时山里女孩子难得一见的一面小圆镜。这小圆镜是金兴江的父母从金家寨街上为她买来的,是和其他的礼品一道送过来的。她厌恶那一大堆的礼品,知道那不仅仅是一堆礼品,更是一根根绳索,收下了,就会把她同金兴江牢牢捆绑在一起了。但是,她太喜欢其中的这面小圆镜了。是这面小圆镜让她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漂亮的面容,才知道自己在叔叔私塾学校,为什么招人喜爱,以至不少男同学常回头盯着她看。她太想占有这面小圆镜了。当初她还很犹豫,几次偷偷地拿起又放下,放下又舍不得。最后,她终于抵挡不了这面小圆镜的诱惑,做贼似地,背着父母,揣进了口袋,带到了笔架山。
一九二六年七月,徐德英以其扎实的古文基础、奔放的思絮以及她那娟秀的文笔,交上了一份同她一样漂亮的试卷,被笔架山学校录取。
进了笔架山学校,徐德英很快就发现,学校虽藏之于深山,却对山外革命的风云变幻十分敏感。五四运动以来,很多进步教师来此讲学,同学之间不仅成立有“青年读书会”,《新青年》和《响导》等一些宣扬革命的书籍和杂志,也在这儿公开流传,同时还建有“演剧社”。“演剧社”是由一个叫周维炯的学生创办的。他们就曾经把自编自演的一个独幕话剧,带到双河山的庙会上去演出。那是一出悲剧,说一个地主借着逼债,要强占贫苦人家的姑娘做他的“填房”,姑娘誓死不从,跳塘时被地主家的长工救了起来,后来,姑娘就同这个长工相爱,二人却在私奔时被地主抓回,感到了绝望的姑娘最后悬梁自尽。当台上演到姑娘悬梁自尽时,台下竟是一片哀叹和哭泣声。就在大家悲愤之时,周维炯往起一站,喊起了口号:“废除封建礼教!”“铲除剥削制度!”口号声响彻在群山之间。据说一个姓冯的狗腿子当场闹事,说这戏“助长邪恶”、“有伤风化”。周维炯痛斥道:“你有没有兄弟姐妹?叫你的姑娘给人家当童养媳,你愿不愿意?你家姑娘为争自由跳塘、上吊,你心疼不心疼?”遭到痛斥的狗腿子灰头土脸。
徐德英听说了这些故事,觉得十分新奇,心灵也受到了震动。遗憾的是,周维炯正是这年的七月毕业,她则刚刚入校,彼此之间“擦肩而过”了。
周维炯的这些故事,别人听了也就听了,徐德英不一样,她不能不联想到金兴江。特别是当她知道,周维炯也只比金兴江大一岁,就已经活得如此轰轰烈烈,做出了这许多令人钦慕的事情,她想,男子汉大丈夫,本就该这样活得有个性,有尊严,敢爱敢恨,可金兴江呢,看上去就是个胸无大志之人,循规蹈矩,萎萎缩缩,相形之下,她更有理由鄙视金兴江了。
但让她吃惊的是,金兴江居然跑到笔架山来看她。一次,两次,她都躲开了,躲开了他也不生气,依然来看她。她终于忍无可忍了,当着同学的面,狠狠地臭骂了他一顿。因为,她心里已经有了自己心仪的偶像,这就是周维炯!
崇拜上了周维炯的徐德英,想方设法了解周维炯的去向,听说他去了武汉,在一所军事学校学习,她竟萌生了要去武汉见他的念头。
一九九一年五月八日,陈桂棣第一次去采访徐德英时,当时她已是七十七岁的高龄了,却依然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出蒋光慈的《我应当去》的一首诗:
什么个人的毁誉!让它去!
重要的不在这里!
但愿在祖国的自由史上,
我也曾溅了心血的痕迹。
徐德英考入笔架山学校时,正值广州国民政府发表《北伐宣言》,武汉被北伐军攻克之时,周维炯等一批中共骨干被派往武汉黄埔军校,亦称“中国国民革命军事学校”。当蒋介石发动了“四一二”政变,汪精卫相继也背叛了革命,周维炯即被派回家乡,以教书作掩护,开始从事农民运动,并在这期间,深入到笔架山,在母校党团积极分子的会议上,传达了党的“八?七会议”的精神。
已经是一名共青团员的徐德英,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学长周维炯。
周维炯这时已是中共商南特委委员兼少共书记,会上,他声情并茂地给大家介绍了周恩来领导的“八一南昌起义”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区“秋收暴动”。
徐德英听了,激动得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。那时,笔架山学校的女学生并不多,在不多的女学生中,能够参加秘密会议的党团积极分子,更是凤毛麟角了。再说,像徐德英这样漂亮的女学生,一直眼睛不眨地、全神贯注地望着周维炯,自然会引起周维炯的格外注意,多看了她几眼,这就更让徐德英激动不已。
周维炯介绍了外面的革命形势后,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时,徐德英站了起来。她想到周维炯领导的“演剧社”在双河山庙会演过的那个话剧。就问:“当年在庙会上演出的那个话剧,是你编的吗?”
周维炯笑着说:“不完全是,是大家。”
徐德英大胆地提出质疑:“有人说那个戏有伤风化,当然不对,应痛加批驳,但是剧中把穷苦人家的姑娘演的不是跳塘,就是上吊,寻死觅活,她好像不应该那样怯懦。”
周维炯不免意外。他想了想,说:“当时那样处理人物,是为了控诉现实的黑暗。”
徐德英显然并没被说服。她又问:“为什么不能像蒋光慈先生的小说《少年漂泊者》的故事那样,在揭露现实黑暗的同时,为广大青年指出一条奔向光明的路——革命的路呢?”
徐德英一点儿不怯场,接着向周维炯提出了更加坦率的意见:“那个姑娘如果不自寻短路,奋起反抗,不放弃必要的斗争,不是会更好吗?”
周维炯被问得一时语塞。
当然,周维炯是完全可以从戏剧艺术的角度,把自己当时的想法加以说明的,但他望着徐德英认真的样子,忍不住笑了,笑得十分开心。
就是这个秘密的党团积极分子会议,让徐德英如愿以偿,见到了自己心中的英雄;也正是这次会议,也让周维炯印象深刻地记住了这个美丽而又敢于直言的进步女青年。
他主动向她伸出了手:“小师妹,你叫什么名字?”
徐德英慌忙站起来。她伸上去两只手,紧紧握住周维炯的一只手,说:“我叫徐德英。”
周维炯这时才回应了徐德英的问题,感慨道:“徐德英同学,你的意见提得好!我们当然不能放弃斗争,放弃斗争就意味着葬送革命啊!”
周维炯的回答,让徐德英十分满意。觉得对方不仅是个大义凛然之人,还是一个谦谦君子。只是,周维炯当时话中的深意,徐德英并不清楚,此时周维炯在秘密从事的,就是“斗争”。他已经等待很久了,正不动声色地在组织一场势必会震惊中国的又一次武装暴动!
二、一生中的黄金岁月
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,没有国民党正规军的驻防,有的只是一些反动民团。这些民团为数不少,相互之间的矛盾却也不少,周维炯觉得在这样的地方起事,极易得手。再说了,三省边区的大别山,山高林密,地势复杂,揭竿而起之后,山高可以御敌,谷深可以藏兵,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武装割据之地。
当然,武装割据,绝非小事,一切计划和行动都只能是秘而不宣的。
首先,周维炯通过曾当过葛县县长的舅舅漆树仁的关系,打入到商南大坤士杨晋阶的民团之中。杨晋阶的民团,有四十多人、十几杆枪,驻守在水陆码头的丁家埠。民团的团丁中除个别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,绝大多数还是被迫当兵的农民。平日,团丁们除帮杨晋阶下去催租要捐外,就是闲游浪荡,欺压百姓,根本不搞什么训练。
周维炯担任了这个民团的军事教练后,就完全按照正规部队的军风军纪和军事技术,严格训练。由于他不打不骂,身体力行,耐心执教,大家军训的热情很高,军事素质迅速提升,杨晋阶看在眼里,自是大为赏识。因此,周维炯很快就成为民团中的大红人,再加上他性情刚直,为人正派,办事公道,不久,丁家埠镇上的市民和周边的农民,都同他混得很亲近,称他为“炯爷”。
“炯爷”接着在民团和在周边的市民、农民中,用易于被大伙接受的烧香结拜兄弟的方式,组织起“兄弟会”,很快就发展了十一名中共党员,并秘密成立了党的支部。
民国十八年,即一九二九年,这年春天,商南一带正闹春荒,周维炯认为时机已经成熟。恰在这时,曾组织过“黄(安)麻(城)起义”的徐子清,和参加过“八一南昌起义”的徐其虚,被派到商南,二人肯定了周维炯的判断,并支持他把五月六日,农历三月二十七,作为武装暴动的日子。
那一天,正是“立夏节”。每逢“立夏节”,山里的人家,有钱没钱,都习惯地要庆贺一下。商南大坤士杨晋阶当然也不例外,那一天又正是轮到周维炯值日,这样,便可以乘着民团的团丁们大吃大喝之际,一举夺枪起义。
一切准备停当之后,那天天刚擦黑,周维炯就吹起了集合哨。一点名,发现少了一个叫田继美的团丁。等到队伍快要解散了,田继美才赶了过来。周维炯很是生气,责问道:“哨子吹了老半天,为什么就听不见?你耽搁了弟兄们吃酒!”田继美不服,叽咕道:“我在解手,哪能听到哨子响。”周维炯忍不住,大为光火,说道:“你还有理了?今晚就罚你站三根香的岗!”
一听田继美被罚站三根香的岗,团丁们无不暗自高兴。哪个团丁爱站岗呢,何况这天又是过节。他们哪里知道,上面发生的这段插曲,其实是周维炯有意导演的“周瑜打黄盖”的一出戏。田继美也是中共党员,这一天晚上的岗哨不仅要控制在自己人手里,其实,当晚的每一桌酒席上,也都暗中安排上了“自己人”。
当菜碗见底、酒桶已空、一些团丁喝得酩酊大醉之时,埋伏在各处的党员团丁,没费吹灰之力便把团部的枪支尽数缴获。随后,便见周维炯从容地站了出来,鸣枪三声,大声宣布:“弟兄们,不要惊慌,我们是共产党,枪支已全部被我们收缴了!”
就这样,丁家埠民团的四十多名团丁,一个不落地都参加了暴动。
就在那一天夜里,随着丁家埠的三声枪响,丁家埠附近的南溪、李集、牛食贩、斑竹园、吴家店、白沙河、汤家汇、禅堂等处的农民,也都按照事先的安排相继发生了暴动。由于那些地方的民团不堪一击,暴动的农民凭着大刀、梭镖,就让团丁缴了械。
第三天,一九二九年的五月八日,各处暴动的队伍会师斑竹园,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,周维炯出任师长,徐其虚任党代表。
此时的徐德英,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,她已经等不得毕业,就向组织上请求,要去当一名红军战士。可是她那一双小脚,行军打仗不方便,而地方上又确实急需要干部,于是她就被派到商城二区四乡苏维埃担任妇联会主席和团委书记。
担任了妇联会主席和团委书记的徐德英,整个人就像喝了兴奋剂,每天都处在巨大的亢奋之中。只见她不辞劳苦地走村串户,动员年轻人参加红军、赤卫队,同大姑娘、小媳妇们一道为前线的指战员打草鞋、洗军衣,去慰问并帮助护理伤病员。
就在周维炯带领三十二师转入外线作战时,狡猾的敌人竟突然乘虚而入,那些逃亡在外的大大小小地主老财,在皖西民团头子柯守恒的带领下,组织起“还乡团”及“清乡队”,杀了回来。他们从佛堂坳直到斑竹园,挨家挨户地搜查,凡当过苏维埃的干部或是红军家属,统统关押起来,一般人员须交几十至一百块银元方可保赎,若是中共党员,便格杀勿论。而商城顾敬之的民团,较之柯守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,他不要钱只要人命,仅花园一处,就屠杀了三千多苏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;周维炯的入党介绍人,也是红色作家蒋光慈的革命引路人詹谷堂,也由于叛徒的告密惨遭杀害。
白色恐怖来得十分突然,徐德英得到消息时,因为是小脚,已无法同大家一道转移,只得简单化了装,躲回到老家洪湾去。所以敢回到洪湾,是因为她想自己不满七岁就到叔叔的私塾学校,接着又去了笔架山学校,这么多年一直在外面,洪湾的人一般不会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。但她并不知道洪湾比她工作的二区四乡更早地已被敌人占领,她的父母已逃离洪湾。
徐德英从来没有走过夜路,更没摸着黑一个人走过这么远的夜路,当她提心吊胆回到洪湾,回到自己家时,才发现门已上锁,家中无人。
显然,洪湾不能逗留了,必须立刻离开。但离开洪湾又能往哪儿去呢?她全然不知。
当徐德英慌不择路地经过一个邻村时,天就麻花亮了,她正准备从村头穿过,冷不防,竟被站在暗处放哨的民团团丁发现。
团丁拉响了枪栓,一声断喝:“站住!你是干什么的?”
骤然就冒出两条大汉,把黑糊糊的枪口对准了徐德英,这让徐德英大吃一惊。她毫无防备,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就在这时,她的身后,忽然又响起了飞快奔跑的脚步声,和一阵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。徐德英下意识地转过身去,这一看,不由得更是一惊。
向她飞快奔跑过来的,居然是金兴江!
怎么会是金兴江?他怎么会在这种时候,这个地方,忽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?
徐德英恍惚如在梦中。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。又认真看了一眼,没错,就是他!
只见这位金家大少爷脸色跑得煞白,跑到两个团丁的枪口前面,不好意思地解释说:“这是我媳妇,我们刚从县城赶回来!”
两个团丁显然认识金兴江,知道他是金家大少爷,听他这样一解释,他们端起的枪,便收了回去。
但是金兴江的解释,却让徐德英大为惊愕。她认为金兴江这是在信口开河。她感到震怒,感到恶心。她想都没想就愤然质问:“谁是你媳妇?别在这胡说八道!”
金兴江却并不介意,反而走过来,强行牵着她的手,更加不好意思地对两个团丁说:“外边兵荒马乱的,我要把她接回来,一路上她都在耍小脾气。”
徐德英见金兴江不仅牵着她的手,还把她往怀里揽,觉得太放肆,伸手给了他一巴掌。
这巴掌把金兴江打傻了。
谁知,两个团丁见了,却乐得哈哈大笑。其中一个说:“打是亲,骂是爱,又疼又爱用脚踹。金大少爷,你小子真有艳福啊!”
就在两个团丁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,金兴江在徐德英的肩上狠狠掐了一把,样子却十分亲昵地去吻她。吻的是她的耳朵,他轻声地警告道:“你要想活命,就听我的!”
徐德英一个激灵,这才清醒过来。她蓦然发现,面前的这个金兴江变得陌生起来,并非自己想像的那般木讷,居然有胆有识,并且有着足够的机智。她不再恼怒,甚至允许金兴江就那样搂住自己,跟着他朝村子里走去。
直到两个团丁在身后消失了,徐德英才充满感激地看了金兴江一眼。回想刚才的一幕,觉得自己多么傻,又多么愚蠢,如果不是金兴江的脑瓜子转得快,后果不堪设想。可是,她十分惊奇地问金兴江:“一大清早,你怎么会在这里?”
金兴江好像又恢复了往日的腼腆与木讷,红着脸望着徐德英,半晌才说:“前两天,我看形势不对,怕你有危险,就打算去通知你躲一躲。半道上却看见你正回洪湾,想上前拦住你,又怕你讨厌我,就偷偷跟在后面……”
徐德英听了,心中一热。她真的想不到,自己最看不起最讨厌的一个人,却对自己这般在意,如此痴情!
不一会,就来到了金兴江的家。来到金兴江家的门前时,徐德英禁不住哑然一笑。她感到自己太可笑。离开洪湾自己的家,却稀里糊涂地摸到金兴江家的村子里来了。
她曾经发过誓,这辈子死也不进金家,可是现在,尽管她打心里依然是一百个不情愿,却还是身不由己地跨进了金兴江家的大门。
徐德英在金兴江的家里一住就是一周。
这一周,她对金兴江家里的情况,终于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。
其实,金兴江的上几代也都是要啥没啥的“穷光蛋”,到了他父亲这一辈情况才有了改变。父母都是能苦能累的庄稼人,几十年如一日,起早贪黑,勤奋劳作,又省吃省用,相当节俭,就积攒下一点钱,置了三十亩地,雇了两个长工。虽说雇用了长工,父母却照样与长工一道上山下田,而且,对长工也从不低看一眼。按说,家里有个三十亩地,放在淮北大平原,算不得什么,可这儿是山区,一闹苏维埃,金家就被划成了“地主”成分,地自然也被分走了一半。好在当年的一个长工当上了村农会主席,对他家还算照顾,父亲已过世,母亲虽被拉去批斗过几回,基本上还算没吃到什么苦。
这些情况,当然只是金兴江介绍的,徐德英有些不相信,询问道:“这一次,穷户从你家分走的地,你们反攻倒算了没有?”
金兴江慌忙说:“娘的胆子小,这样的事,她哪敢!”想了想,又讨好地说:“其实我父母都是善良厚道人,辛苦了大半辈子,也就这几年日子才过得富裕点。”
徐德英立刻警惕起来,她严肃地告诫金兴江:“你别对我胡思乱想,我们不是一个阶级队伍的人,这点,你可要记清楚!”
说得金兴江勾起了脑袋,不再吱声。
徐德英一周没出门,就住在金家后院的一间厢房里,虽蜗居在厢房里,通过金兴江的暗中打听,外面的情况大体还是了解的。民团头子柯守恒,在家私设公堂,一切最残忍的手段都用在了红军家属和苏维埃干部身上;商城顾敬之民团更凶残,非但滥杀了三千多革命干部和群众,还杀害了鄂豫皖三省边区最早的共产党人詹谷堂。当然,更让她吃惊的还是,在这次的反攻倒算中,周维炯在河南省民政厅当司法处长的小舅漆树德,竟协同柯守恒和顾敬之的民团回到商南,直接参与了对红军家属的迫害,并趁机倒算已经被农会分给了群众的大批财物。
金兴江带回来的有些消息,徐德英很难相信,就问金兴江:“你没搞错吧?周维炯打入丁家埠民团,靠的就是他舅舅。”
金兴江说:“不错。帮他打入杨晋阶民团的,那是当过葛县县长的大舅漆树仁,这是小舅漆树德。”
徐德英依然不相信:“你这么肯定,他小舅就真的干了这种坏事?”
金兴江很委屈,于是作了详细介绍:“曾经分了他家财产的两个红军家属,听说漆树德回来了,曾躲到我们村的一个亲戚家,漆树德知道后,亲自带人找过来,硬是把躲在这的两个红军家属,活活劈死。这事许多人都亲眼看到。”
徐德英不再说话,她感到这个世界太复杂。
受到金兴江母子二人的盛情款待,徐德英不愁吃,不愁喝,而且十分安全,她却仍不免感到度日如年。她隐隐感到一种耻辱,觉得自己是躲在地主的家里在苟且偷生。她差不多是一天天数着日子过的,因此,清楚地记得,这年的九月十二日,周维炯率红三十二师以风卷残云之势杀回商南地区,给柯守恒和顾敬之的民团和以及地主老财的还乡团以致命地打击。据说,正在鄂东征战的周维炯,得知家乡遭到敌人的反扑,牺牲了那么多的干部群众,其中,就有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詹谷堂,他懊恼得只差没吐血。
在干净彻底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、气焰嚣张的反动分子之后,周维炯就在詹谷堂牺牲的南溪,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。徐德英也赶到南溪,参加了这次大会。
大会上,受害者家属纷纷上台声讨敌人的滔天罪行,有人也控告了漆树德对红军家属和苏维埃干部疯狂的反攻倒算。
徐德英见有人当众揭露漆树德,心中咯噔一跳。漆树德的罪行,当然应该揭露,但她觉得不该在周维炯主持的大会上,这样当面锣、对面鼓地“敲打”起来。
然而,周维炯并没有回避,说:“共产党的政策,对谁都是一样。别说漆树德是我亲舅,谁要干了对不起老百姓的事,就是老子娘也不行!”
周维炯的公开表态,赢得了全场雷鸣般掌声。
他还说,他对他的这个小舅是非常了解的,在组织上派他去武汉军校学习时,漆树德就百般阻止,说他这是“起浪头”,“图时新”,警告他说,“共产党将是乱国之寇,必须多加小心。”他相信大家对漆树德的揭发,会是有凭有据的。
经过调查,周维炯感到漆树德确属民愤极大,于是会议期间,他就派人把漆树德抓了回来。
抓了回来的漆树德,见到周维炯,居然端出长辈的架子,当着众人面,指着周维炯破口大骂,并上前要打周维炯。
周维炯实在忍无可忍,命令警卫员:“把他绑起来!”
警卫员知道漆树德是周维炯的亲舅,绳子找来了,却不敢动手。
漆树德见没谁敢动手,越发狂妄起来,认为周维炯不过是把他抓来吓唬一下,也不敢把他怎么样。便放出话来:“就凭你们几个毛猴子兵,几支破枪,就想造反?实不相瞒,我已写信到开封,不出十天,就会有大队人马来围剿你们。你们现在反悔,向国军投诚,还来得及,有我九爷(他排行老九)给你们担保。”
周维炯一听,怒火中烧。马上应道:“你居然还想着搬救兵来围剿红军,与人民为敌到底,好啊,好!我们等着,他们不来,我们还要去找他们呢!”
说罢,他抓过警卫员手中的绳子,自己动手将漆树德捆了起来。
这时候,漆树德的老婆,带着三十多位族亲,还挑了一挑子银元地契,赶来保释漆树德。
周维炯对送来的银元和地契,照单全收,但道理也摆在明处。他说:“你们都是我的父老乡亲,共产党也不是不讲人情世故;但我是一个革命军人,小舅他勾结反动民团头子柯守恒和顾敬之,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,还写信到开封去搬国民党军队企图围剿红军,实属罪不可恕,理应得到人民的惩罚!”
漆树德老婆哭得鼻子一把眼泪一把,“好外甥”、“亲外甥”地向周维炯说情,说只要饶了漆树德这一次,放他回去,愿全家财产都充公。
周维炯哪管面前的这个舅母如何哭喊,为平民愤,仍命警卫员把漆树德押到了大会上。然后,予以处决。
漆树德被处决后,周维炯的母亲也赶到了南溪,她虽然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一向不喜欢她,常骂她是贱骨头,不该嫁到穷鬼周家,但毕竟是姐弟骨肉至亲,听说漆树德已经被周维炯处决,就老泪纵横,瘫倒在周维炯的跟前,说:“孩子,你革命,也不能不讲一点仁义啊!你这样绝情,叫我往后怎么去见娘家人?”
周维炯说:“娘,小舅和我们不是有什么私仇,他是血债累累的反革命,不杀他,我还怎么革命?”
母亲伤心地望着周维炯问:“儿啊,你参加革命,除了革命,就啥都不要了?”
周维炯觉得一时半会给娘解释不清,便干脆说道:“除了革命,儿可以啥都不要!”
“娘也不要了?”
周维炯忙上前扶起母亲,说:“你又没干啥坏事,你的养育之恩儿怎敢忘记?”
母亲怔怔地,又问:“她,你是不是也不要了?”
周维炯知道母亲说到的“她”,是他的表姐,那是他的未婚妻;一对青梅竹马的伙伴,两小无猜,过去一直在热恋着。他说:“娘,革命成功了,我们就成亲;你就别再操这份心!”
母亲依然忧心忡忡流着泪说:“你千万不要光顾着眼前,日子长着呢,可要小心啊!听说好多人出大钱要买你人头,我在家提心吊胆,天天都替你祷告几次呀!”
周维炯说:“娘,不怕,你不是也看见了,群众都向着我们嘛!”
在南溪召开的群众大会,开了整整三天。周维炯的大义灭亲感动了成千上万人,会议期间大批的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,红三十二师得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大发展。
会后,徐德英重又回到了商城二区四乡苏维埃政府,仍干她的妇联会主席和团委书记。到了这年的十月,周维炯获得一个情报:商城县的民团和顾敬之的民团因征收捐税,分赃不均,正混战于商城的北乡,县城里只有警卫队和红枪会的二三百人留守,此乃天赐良机,于是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:“智取商城!”
周维炯首先在师部的手枪队挑选出十六名精明强干的指战员,化装成卖油条的商人和卖菜的农民,趁着天亮前混进城去,控制住四个城门的岗楼。然后,将全师隐蔽靠近,一旦岗楼被端掉,便全线发动总攻,给守敌一个措手不及。
这是红三十二师成立以来,第一次攻打县城,周维炯知道,此役只能胜,不能败,所以行动之前,他在部队进行了一次总动员,还组织起部分区乡的赤卫队予以配合。
徐德英听了传达后,兴奋得一夜没睡,主动请缨,并亲自带领二区四乡参战的青年赤卫队员,赶赴指定地点待命。
由于事先对城里敌人的分布和防御情况了如指掌,战前又作了最充分的准备,因此,四个城门的岗楼如期得手,随着一声激越的冲锋号骤然响起,埋伏在各处的红军和赤卫队员,就潮水一般地从四面八方向城里猛扑过去。这时,敌人刚刚起床,遭此突袭,乱作一团。周维炯则带人直取县衙,和敌警卫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。他手持双枪,左右开弓,弹无虚发,敌人招架不住,纷纷缴械投降。徐德英也带着她的青年赤卫队员,协同红军,冲入了敌人红枪会的队部。
没用一个时辰,红旗便插在了商城县政府的楼顶上。
商城解放了,商城县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。就在庆祝商城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的庆祝大会上,徐德英第一次听到了后来被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: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——
八月桂花遍地开,
鲜红的旗帜竖起来。
张灯又结彩,
张灯又结彩,
光辉灿烂现出新世界;
亲爱的工友们,
亲爱的农友们,
唱一曲国际歌庆祝苏维埃!……
热烈而又悠扬的歌声,赢来了阵阵掌声,徐德英竟被这支歌感动得热泪盈眶,跟着使劲地鼓掌。她想不到歌声居然可以像箭一样,像朝霞一样,像春风一样,让人心动,让人陶醉,让人提神长劲。
她一阵阵发愣。所以发愣,是因为她对这支曲子并不陌生。她知道这曲子原是来自大别山的一首情歌。这首情歌原先的歌词她太熟悉了,大家就叫它《小小鲤鱼》——
小小鲤鱼是红腮,
上江游到下江来,
头摇尾巴摆,
头摇尾巴摆,
小小金钩将你钓起来,
不为冤家不钓你起来!
谁曾想,一首再普通不过的情歌,在这里变成了一首革命歌曲;男女情爱原本同革命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,只是改动了一下歌词,就把对爱情热烈的倾诉,变成了对革命理想的热情赞颂。
当然,徐德英不知道,这支革命歌曲不久就由大别山传到了中央苏区的井冈山,后来随着红四方面军西撤入川,又把它带到“天府之国”,最后带到了延安。其实,延安黄土高原上的那个李有源,同样是把流传在陕北的情歌《跑白马》改编成了一度风靡全国的《东方红》。
徐德英从县城回到二区四乡,在二区苏维埃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,她带领四乡的文艺宣传队,在大会上表演了一个引起不小轰动的节目。那节目是一个大合唱,合唱了一首革命歌曲。歌词就是徐德英亲自操笔的,她将流传在家乡的一首情歌重新填词。
原词是——
郎在田里薅黄秧,
姐在塘边捶衣裳,
郎薅三下望着姐,
姐捶三下望着郎,
望着郎,
棒槌打在石头上!
徐德英将它改写成了一首颂扬周维炯的革命歌曲——
工农士兵齐暴动,
大别山上太阳红,
五月六日立夏节,
武装起义成了功,
成了功,
不忘英雄周维炯!
这首歌不仅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,还很快传到了周维炯的耳朵里。周维炯听说歌词是商城二区四乡苏维埃一个女干部编写的,说这女干部才年方十五,十五岁就担任了妇联主席、团委书记,很了不起,是个人才,就想见一见。
周维炯想见一见“女主席”的消息,传到徐德英这儿,她激动得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。这天,她鼓起勇气,骑上一匹大白马,径直去了红三十二师师部。
当梳着一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,身着蓝底白花对襟褂和阴丹士林长裤的徐德英,突然站在周维炯的面前时,他竟被眼前如花美貌的徐德英,惊得一个愣怔。他好奇地问:“小姑娘,你找谁?”
徐德英面对自己心中的偶像,本来还有些心慌气短,听对方这么一问,不免感到几分委屈:“怎么,当了师长,就不认识我了?”
周维炯很是诧异:“我们见过面?”
徐德英毕竟已经做了将近一年的群众工作,与各色人等打过不知多少回交道,算是见过世面了。她口齿伶俐地说:“当然。你再想想,过去你是不是去过笔架山学校?”
周维炯猛然想起来了。想起了那个目不转睛听他说话的女学生,想起了那个给他编写的话剧直陈意见的漂亮的师妹来。马上问道:“你是徐德英?”
其实,他们也只是那次的一面之交,周维炯竟然记住了自己的名字,这让徐德英很是兴奋,兴奋得脸上飞起了红云。周维炯见了,倒变得不自然起来,连忙解释:“你当时指出不该放弃必要斗争的意见,我印象很深,所以就记住了你的名字。”
说着,为徐德英倒了一杯水,示意她坐下,问道:“今天你找我有事?”
徐德英一听,立即反问:“听说你要见见我,你找我有事吗?”
徐德英这一问,又把周维炯问住了。但他很快意识到,这位小师妹就是商城二区四乡的妇联会主席、团委书记,便笑着问:“《不忘英雄周维炯》的歌子,是你编的?”
“是呀,不好吗?”
周维炯收起了笑容,说:“不好,很不好。”
“为什么?”这让徐德英感到意外。
周维炯沉吟了一会,严肃地说:“我就是一块铁,也打不了几根钉。‘武装起义成了功’,那是大家的功劳,你这么一宣传,不是把我放在火上烤了吗?没有商南特委书记徐子清的支持,没有党代表徐其虚以及那么多干部战士的奋不顾身,敢打敢拼,我一个人就能成事?”
徐德英想想,周维炯说得不是没有道理,不过她并没被完全说服。红着脸问:“就为这事,你要见我?”
周维炯于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:“红三十二师现在发展壮大了,有的是枪杆子,就缺笔杆子。作为一支战斗部队,首要的当然是打仗,要能打硬仗,打胜仗,但宣传工作一样的重要啊!你如果愿意,可以到我们师部来搞宣传。”
徐德英做梦都想成为红军战士,她一下站了起来,双脚并拢,向周维炯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,同时大声喊道:“报告师长,红军宣传员徐德英现在前来报到!”
周维炯被逗得哈哈大笑。不过他却严肃地提醒:“欢迎你的到来。但今后不准再宣传个人,这应该成为一项宣传纪律!”
徐德英的两腿再一次并拢,响亮地回答:“是!”想到自己在地方的工作,于是问:“那,我在二区四乡的工作怎么办?”
周维炯说:“地方政府,我会打招呼。”
DSP广告投放运营哪家看白癜风的医院好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huaibeizx.com/hbsjt/9083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