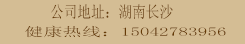![]() 当前位置: 淮北市 > 淮北市交通 > 洪泽记忆岔河老街1980年代的琐忆
当前位置: 淮北市 > 淮北市交通 > 洪泽记忆岔河老街1980年代的琐忆

![]() 当前位置: 淮北市 > 淮北市交通 > 洪泽记忆岔河老街1980年代的琐忆
当前位置: 淮北市 > 淮北市交通 > 洪泽记忆岔河老街1980年代的琐忆
岔河老街年代的琐忆(一)
文:龚浔泽图:仲肇舒
淮宝县的留痕
不是每个人都有老家,更不是每个人的老家都有一个老街。对于我来说,有一点幸运的在于,想到老家时,不仅有一座老街可以追念,而且体味了它的变“老”。这个老街叫“岔河老街”。
其实,江苏有3个叫岔河的乡镇,一个在北面徐州邳州,靠近山东;一个在南面的南通如东,靠近黄海;还有一个在淮安洪泽。三者的连线像一个钝角三角形,而淮安的这个岔河是顶角。
3个岔河估计都有老街。但淮安的岔河,显得相对特别一点。这个特不在于它的今天,而主要是在于它曾经的一段历史,在于建国后江苏行政区划史跳不过的一个篇章。抗战期间,南下的八路军和北上的新四军苏北会师后,在淮阴县、淮安县与宝应县之间接壤的地方成立了淮宝县,岔河老街便是它的县城。这个县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,到年精兵简政时才被撤销。因此,回顾建国初的江苏行政区划,绕不开淮宝县,绕不开淮宝县的撤销,绕不开淮宝县撤销时的县城。因为这段情况,在建国前后的江苏历史材料和相关地图上,很容易找到“岔河”。
那时候,南通岔河所在的如东,因如皋之东而得名,也才刚刚建立,不同的是,如东躲开了精简,延续了下来,而且它那时的县城还不是现在的掘港,而是岔河边上的马塘。邳州的岔河,现在经济据说不错,但这个岔河到新世纪后才撤乡建镇,可见其历史底蕴的深浅。这是洪泽岔河的特别之处,也是它在周边乡镇中相对特殊的地方。这段历史,在今日岔河乃至洪泽都还残留着余韵。洪泽县城原来东西向的第二主干道叫淮宝路。岔河镇80年代新建镇区的主干道叫淮宝路,岔河镇政府所在的地方也叫淮宝居委会。这些都是那段历史的印记。
不过,对于一个建国30年后才出生的人来说,这段历史毕竟有点远,没有亲历的深刻。即使后来了解到,很多也不是听到的,而是读到的。这就使它的这些辉煌的过去,给我的感觉远没有我经历过的真切。
独特的才会普遍,凝固的才有永恒。即使岔河在民国时叫过岔河区、岔河市、岔河镇,但我记忆中定格的老街,不会叫岔河镇,而是叫岔河公社或岔河乡。等叫岔河镇的时候,新镇区已经在西面慢慢建设起来,这一片街区却变成了“老”街,失去了街和集市的功能。等到大家后来真正意识到它的一些价值的时候,它却真的老了,而且快消失了,或者在以保护的名义被消失。新生或许必然伴随着老去。成长必有代价,清醒终究会有感伤。
医院
在我的记忆中,首医院,老街首先意味着一种幸运。
老街的北街,与中街之间横亘着浔河,在浔河之上架着一座有年历史的石板桥。石桥净高不高,桥下走不了机帆船,后来便在北街的西、北、东三面重新开挖了一条河道,绕过石桥,这也使北街变成了浔河中的一个岛。
医院就位于北街的东头,几乎三面临着浔河及其新开的岔道。医院我已经没有直观的印象了。但开始懂事的时候,医院来开我的玩笑。说你早知道你这么调皮,当时还不如把你送到东滩去,或者说你是“巧”来的,不然就应该在医院的茅厕坑里了。
再大一点的时候,方才了解到的,洪泽县年成立,年将长期属于淮安县(民国之前叫山阳县)的岔河公社划给洪泽县,由于人口少、历史负担小,洪泽县的很多工作相对容易开展。
70年代开始抓计划生育后,洪泽县的计生工作便在苏北地区一马当先,不与淮北地区比,单在江淮里下河地区也堪称模范。岔河位于洪泽的东部,东面直接连着诞生“柳堡的故事”的宝应县,具有典型的里下河地区风貌,很多工作一直又是洪泽县里的模范,计划生育更是如此。
年的春天,洪泽正在掀起一个计生的高潮,岔河便处在这次高潮的漩涡。如果再晚10天,只能跟其他跟我差不多同时怀孕的二胎、三胎一样,被送到医院“引产”了。大人曾经常点名道姓地说谁谁家的小二子、小三子,就被扔在东滩厕所的茅坑中沤肥了。讲得我毛骨悚然,不知道是信还是幸。对于我来说,真是巧得有惊无险,既巧在预产期没有再靠后,更巧在我孕期一足月就生了。这个巧,也使得我成为老家最后一批不用罚款、家庭不受牵连的二胎。
这个出生前的插曲,使我回忆幼年时总也跳不开老街。
八百年石桥
现在的石桥南头有城门样的建筑,由南向北走上石桥要穿过这个门洞,上面写着“柘塘故里”几个字。这个完全是后来建的,属于典型的新文物。过去不仅没有这个镇门镇墙,而且石桥上也没有栏杆。
印象中的石桥最早的形态是:河中两个桥墩,把桥分成南北纵向的三截,每截并排有4块桥板,一看桥板就是有了年头的,板面光滑得像面镜子,滑到行人毫无悬念,更让人担心的是桥板之间还有很大的缝隙,桥面两侧也没有任何可以扶持的把手。
对于这座桥,我走过的次数不多。但街上的同学特别是桥南的同学印象都很深。那个时候幼儿园在桥的北侧。他们去上幼儿园时都要路过石桥。这些每次要路过石桥才能去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后来谈起这座石桥,都有些后怕。对于这种怕,平时就有点担心,下雨的时候更是胆战心惊。也难怪他们会有这个阴影,那个时候,小孩上学基本上没有大人护送,如果小孩上学有人护送被同学发现了,实际上是会被羡慕的,但首先表现出来的一定是被嘲笑。
想象一个下着雨又刮着风的清晨,一个幼儿园的小女孩,没有人护送,穿着小红靴,打着小红伞,桥下是湍急的浔河谁水,走在不宽的桥板上,注视着脚下桥板上的缝隙,抖抖豁豁地挪过石桥去上学。那种胆战心颤是会传染的。
有一次我上街的时候,看到石桥上有人在施工。下一次再见到石桥时,两侧已经有了金属栏杆了。再过一些时间,桥上石板之间的缝隙已被水泥砖块填上了。20年后再去看时,石桥的金属栏杆又被混凝土栏杆替代了,石桥的南头也多了一个过去记忆中不曾存在的“柘塘故里”街门。
尽管八百年来石桥南北的街、人、景不停在变,尽管石桥老了却又焕发新象,但石桥的位置没变,建筑主体没变,站在石桥远眺东西两侧浔河河面的感觉没变。
中街路口
老街中街,如同它的“中”字,意味着中心和繁华,这种热闹给了小时候的我一次印象深刻的考验。
当时的供销社似乎在中街与西街的交叉口,围绕这个交叉口次第分布着一些杂货店,这就使这段不长的街道俨然成为老街的商业中心。农历逢二、逢五、逢八,便会迎来岔河街的“逢集”。这个时候四面八方的商贩和赶集的人会拥挤到这里,挤得不宽的街道几乎水泄不通、寸步难行。
那时候农村的孩子比现在闭塞多了,大人管、带孩子也没有现在这么尽心。我家虽然离街很近,但毕竟不是生活在街上,作为一个幼儿,上街的次数屈指可数。
虚5岁那年,镇上南街的一个亲戚家添丁办酒席,家里人带我去祝贺,大人们有大人们的事情,我就跟镇上亲戚家的孩子以及他们邻居家的孩子一起玩耍,他们几个虽然跟我年龄相差不大,但常年生活在街上,对巷子里弄非常熟悉,哪条通哪条不通,哪条通往哪里,那肯定是熟悉的,可我不熟,于是跟着他们三转两转就转到了主街上。
那天恰好逢集,人多嘈杂,很快我就看不到他们的影了,也找不到回到大人那里的路,努力找了几下,还是不行,于是便慌了,站在中街的拐角处哭了,很多人便围观上来,问我家住哪里,父母叫什么名字,我哪说得上来……
有一个热心的阿姨,看我虎头虎脑的,神态似乎也有点面熟,便把我拉到供销社商店的门槛上坐着,陪着我说说话,安慰我,我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。也许时间并不算太长,但在我印象中总是觉得过了好久。突然间,看到前方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,那是我爷爷,像见到救星式的,我迅速地跑了过去,抱住他哇哇大哭起来。
其实,爷爷倒不是来找我的,家里人以为我跟那几个街上的孩子在玩,还没有发现我走丢。爷爷刚好要去中街北面一点的店铺去买东西,才路过这里。
那个时候的乡村,方圆数里,应该都是认识的,不像现在。那些人见到爷爷,彼此本就熟悉,就告诉了爷爷发生的事情。爷爷赶忙安慰我,也谢谢各位街坊。
过去这么多年了,那天的场景还依旧清晰,每每路过那里,都感到有趣、有情。如果那个场景迟后几年,会不会遇到人贩子,从此被带得远离他乡,换了一种人生。我想谁也不敢打包票吧。
东街澡堂
老街东街最短,但那里有一座澡堂,也使东街不长却不乏人气,成为老街温暖的象征。
印象中的儿时冬天比较现在的冷,那个时候到了冬天,岔河的水面,不提家前屋后的河渠,连通湖的浔河、十里长河都封冻起来,不像现在,冬天的河面已经很少结冰了。
淮河以南的地方,到现在有暖气的小区都还不多,那个时候的农村更不知道什么叫暖气。没有暖气,加上空气又比较湿润,冬天的室内实际上比室外还冷。唯一取暖的方式就是火盆,用泥和上草做成盆的样子晒干,将点燃的木炭和灶台火塘里尚有余热的草灰放在其中,人坐在边上会稍微暖和一点。
在这样的环境下,容易挨冻的人,首先是孩子,手上脚上生有冻疮是普遍的,方言称之为“冻果子”。最容易生的部位是手指、手面、脚趾、脚后跟,还有耳朵,都是血液循环的末梢,肿得鼓鼓的,隐隐的疼。有的小孩手面、手指全部是冻疮,肿得像个馒头,一张小手仿佛从平面变成了球面。冻疮每次痊愈,只能全凭气温自然回升,才能最终消下去。于是,有了冻疮后,便希望天热起来了;但偶尔热一下,冻疮又让人痛痒难忍。
天寒地冻的时候,最舒适的便是在热气腾腾中洗把澡。
但痛快地洗把热水澡,对于那个时候的大多数乡村来说,是难以企及的。对于那时村里的人来说,冬天洗澡是一件奢侈的事,最怕的就是洗澡。
那个时候的乡村,热水器、浴霸像天方夜谭,亚克力或陶瓷浴缸也远未普及。如果在家里洗澡,要买浴帐、浴盆,要用灶台烧很多的水,要折腾半天,一不小心就可能受冻感冒。
上初中时有一个离街比较远的同学,说他一个月才洗把澡,让我惊讶不已。
后来想想也情有可原。当时全乡镇只有一座位于老街的公共浴堂,对于住在镇上及周边的人来说,洗个澡相对方便,但对于乡下离街远的人来说,那洗澡就很不方便了。乡下人本不常上街,上街也未必舍得次次都去这个澡堂洗澡,洗一次澡像过一次节一样也未尝不可的。
我家到澡堂步行只要多步,因此洗个澡虽然没有街上的人方便,但终究并不费事、麻烦。于是,冬天每周都能洗一次热水澡。一般是傍晚放学回家后,爸爸喊上我,有的时候还叫上表弟、堂弟,大家一起,用袋子装着换洗衣服,兴高采烈地朝澡堂走去,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边跑边跳。
澡堂在东街的一个院子里。房子是用青砖砌的,屋顶是细瓦,零散的长着一些草。
说是澡堂,其实真正供洗浴的只有一间10来平方米的房间,里面隔成四个长方形的浴池,水温由外到里依次变高,最里面的一个池子温度最高。
据说最热的池子下面就是加热水温的火塘。工人就在后面不停地添柴,维持着浴池的水温。这个最里面的池子也就是“锅”了。
这个浴池,用现在的眼光看,其实并不卫生。但那个时候,却觉得真是一种享受。
紧挨着浴池房的,是一间比浴池还小的房间,向外连接着更衣的地方。这里有一排小便池,也有一个永远不关的窗户,使得这里温度稍微低了一点。从热气腾腾的浴池出来,是一种享受,但刚脱下衣服前往浴池路过时,却会打一个寒颤。
即便浴池边有一个这样通风的地方,也不宜在浴池里久泡。特别是感冒或者体虚的,更不宜久泡。经常有人会在里面热得发晕。
澡堂里有一个擦背师傅,大家都称他“张二”,他是我们村的,是我姑姑家的邻居,对表弟和我倒是挺和善的。外面卖票的人好像换了几茬,但擦背的师傅却一直是他。有的时候他在浴池里给人擦背,有的时候在这个隔间给人擦背。他的体质很棒,同时还肩负着浴池里救生的任务。
再外面是供更衣的地方,那个空间却不小,有两个大的开间,一个东西向的,有7、8间房,还有一个南北向的,有3、4间房。靠着墙的四周砌的一圈不高的台子,上面铺着草席,洗澡时把衣服脱在草席上,各人把各人的衣服包成一堆即可。没有柜子,澡客若有什么贵重的东西,可以交给门口前台卖票的保管即可。
澡堂生意最好的时候肯定是大年三十,也就是除夕。这一天,澡堂会在凌晨3点左右开放。为求彩头,澡堂主办方会在澡堂的一些拐角放些小的年货或红包,去的早,不仅可以洗清水澡,而且可以抢到红包。对于孩子来说,想想都是激动的。但我们家远,也不愿意起早,关键是去的也未必能抢到,小的时候大人一次都没带我那么早去过。等我长大后,自己也没有了抢的兴趣。
澡堂建在什么时候,我没有问过,感觉应该有一些年头了,起码应该民国就有了。父亲小时候就是爷爷带着在那里洗澡,我们小时候先是爷爷、父亲带我们去洗澡,再大一点,有时也是我跟堂哥陪爷爷在那里洗澡。
老街渐渐衰落,但这个澡堂却长期盛况未减。等到新街上的澡堂开了好几个,乡下一些村里也有澡堂了,条件也都更好,但这个澡堂还是坚守了一段时间。直到后来,太阳能热水器、电热水器逐渐普及,洗澡更加容易,到公共浴室的人也慢慢少了,这个澡堂才作为老街上最后的一个服务业态淡出舞台。一个澡堂满足全镇人洗澡的景况也再也不会有了。上次回家,感觉房子都已经坍塌殆尽,不由地感伤。
征文启示
如果你对家乡有说不完的话
如果你眼中的家乡有着别样的风景
又或者你拥有十分珍贵的老照片
都可以告诉我们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huaibeizx.com/hbsjt/9072.html